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从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看闽台地缘关系)
 摘要: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随着移民在台的拓垦经营牢牢扎根于台湾土壤, 并成为历史的文化积淀。日据时期殖民者虽对台湾早期地名加以变更, 许多地名也只能在承认和利用闽南语读音的基础上进行蜕变,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闽台间紧密的地缘关系。关键词:台湾地名; 闽南方言; 闽台地缘关系
摘要: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随着移民在台的拓垦经营牢牢扎根于台湾土壤, 并成为历史的文化积淀。日据时期殖民者虽对台湾早期地名加以变更, 许多地名也只能在承认和利用闽南语读音的基础上进行蜕变,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闽台间紧密的地缘关系。关键词:台湾地名; 闽南方言; 闽台地缘关系
台湾社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 早期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 大陆传统文化的传播始终离不开人口这一载体。大陆人口迁移台湾, 实质上也是一种原乡文化的迁移运动。而语言作为一种空间符号, 是这种文化的重要表达载体。在早期移民流动过程中, 那些原乡文化要素又总要将其具体内容烙印在方言上, 其中很明显的就表现在台湾早期的地名上。
早在宋元之时, 福建漳泉沿海地区的人民就曾迁移过台。如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记载了当时晋江县附近移民到澎湖岛上耕种谋生一事: “海中大洲号平湖, 邦人就植粟、麦、 麻 ”;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里也提到了大陆人民在台生活的情景: “岛分三十有六, 巨细相间, 坡垅相望, 仍有七澳居其间,......泉人结茅为屋居之 ”。到了明代, 漳泉之人迁往台彭的人数更多, “屹然一大部落”。顺治十八年 ( 1661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随带水陆官兵及眷口达三万多人; 其后郑经入台又带去官兵及眷口约六七千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闽南人。迨至清代, 大陆人民渡台仍源源不断, 其中又以福建漳泉两地为主。据1905年日本殖民当局所做的第一次台湾户口调查显示, 台湾人口已达 304 万人, 其中漳泉两语系共有 230万人, 约占 80% 。可以说, 这一大移民群体的存在, 对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在台湾地名中保持稳固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拟将台湾地名研究置于移民背景下, 探讨清代台湾地名中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的形成和积淀过程, 并对日据时期台湾地名中这一文化要素的变化作一分析, 以此来探讨闽台间的地缘关系。
1
清代台湾地名中闽南方言
文化要素的形成与积淀
台湾早期地名, 绝大部分是以原住民语为语源的, 这些地名没有文字可记录, 多以口承的方式流传。大陆移民在台开垦中遇到此类地名, 多以方言译音。由于渡台的人口中闽籍移民占绝大多数, 其中尤以闽南人为主, 因而移民在音译或命名时主要以闽南语为基础。
如台北市北投区旧名为“北投社 ”, 原为凯达格兰族内北投 K ipatauw 社址, 清代属淡水海防厅, “北投”系用闽南语音 Bak-tau音译 (该词的凯达兰语读音为 Patauw);桃园县大溪镇, 位于大汉溪东岸, 平埔族霄里社称大汉溪为 Takoham, 清代大陆移民音译成“大姑陷”, 后改名“大嵙崁”,系用闽南语 To -khe-kham 音译而成; 台中县大甲镇, 清初“大甲社”为蓬山八社之一, 属淡水海防厅。“大甲 ( To -kah)”乃得名于平埔族道卡斯族名 Taokas之音译; 台中县丰原市旧称葫芦墩, 闽南语音读 H -tun, 系音译巴宰海族 Huluton社; 彰化县北斗镇旧称“宝斗”, 康熙年间开拓, 旧名为东螺堡, 又名宝斗。移民以“宝斗”闽南语 Bao-tu音译巴布萨族东螺社Baoata , 后改为“北斗”;二林堡清代分为二林上堡、二林下堡, ”二林是以闽南语 Nng-lin音译巴布萨族G ielim 社而得名, 现为彰化县二林镇; 台中县大肚社, 雍正年间以福建漳州府赵、王、 陈三姓移民为开拓主力, “大肚”一名乃以闽南语 To-to音译平埔族拍瀑拉族大肚社Tatuturo。1897年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在台湾埔里六社原住民住地作调查时就曾指出该地“古来至今, 语言已完全中国化......他们连小孩、妇女都已能用流利的台湾中国话”, 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的“中国话”即指闽南方言。埔里一地尚且如此, 其它地方用闽南语音译台湾早期地名的情况犹可信也。
-tun, 系音译巴宰海族 Huluton社; 彰化县北斗镇旧称“宝斗”, 康熙年间开拓, 旧名为东螺堡, 又名宝斗。移民以“宝斗”闽南语 Bao-tu音译巴布萨族东螺社Baoata , 后改为“北斗”;二林堡清代分为二林上堡、二林下堡, ”二林是以闽南语 Nng-lin音译巴布萨族G ielim 社而得名, 现为彰化县二林镇; 台中县大肚社, 雍正年间以福建漳州府赵、王、 陈三姓移民为开拓主力, “大肚”一名乃以闽南语 To-to音译平埔族拍瀑拉族大肚社Tatuturo。1897年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在台湾埔里六社原住民住地作调查时就曾指出该地“古来至今, 语言已完全中国化......他们连小孩、妇女都已能用流利的台湾中国话”, 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的“中国话”即指闽南方言。埔里一地尚且如此, 其它地方用闽南语音译台湾早期地名的情况犹可信也。
在开垦过程中, 移民常常用原乡的方言文化要素来命名新垦地。在这些民间地名中,“闽南语语源的地名占绝大多数, 这类地名是随着闽粤垦民赴台开拓的进展而增加起来的”, 它凝聚着移民从原乡带来的多种文化要素, 如地名命名习惯、地方性的地名惯用语、 生产和生活习俗等, 其中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对台湾早期地形地物、 经济活动的地方性习惯用语表现尤为突出。下面以清代闽南方言常用地名“厝、 寮、 埔、 坑、陂、 崎、 墘、 尾”等为例, 从清代府志、县志等史料中对比分析此类地名命名在大陆闽南、 台湾两地的具体用名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清代闽台地名命名惯用语对照表

以“厝 ”为例,闽南方言称房屋为“厝”, 如南安县的内厝、后厝等; 厦门的吴厝、张厝、黄 厝、吕厝等。大陆闽南这一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命名, 在台湾也具有同样的方言和命名习惯, 而且带“厝”的地名多与房屋数目、位置、构造及祖籍地、姓氏等相结合, 如清代苗栗县的六块厝、头厝、头前厝、泉州厝、同安厝、刘厝、张厝等, 尤其是冠籍、冠姓地名的存在, 更是体现了大陆移民对祖籍地深厚的情感。这种相同的方言地名命名习惯, 在其他惯用语 (如寮、埔、坑等 )里也随处可见。
”为例,闽南方言称房屋为“厝”, 如南安县的内厝、后厝等; 厦门的吴厝、张厝、黄 厝、吕厝等。大陆闽南这一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命名, 在台湾也具有同样的方言和命名习惯, 而且带“厝”的地名多与房屋数目、位置、构造及祖籍地、姓氏等相结合, 如清代苗栗县的六块厝、头厝、头前厝、泉州厝、同安厝、刘厝、张厝等, 尤其是冠籍、冠姓地名的存在, 更是体现了大陆移民对祖籍地深厚的情感。这种相同的方言地名命名习惯, 在其他惯用语 (如寮、埔、坑等 )里也随处可见。
此外, 清代台湾地名中还留存着许多富有闽南方言特色或专用意义的地名, 如恒春县的沙尾堀、凉伞兜;淡水厅的桶盘屿、茇林、乌树林、乌眉崎、 松仔脚、樟树窟、查某旦、大水堀;苗栗县的风空吼、泉水空、牛相觸,还有 莱宅、猪厝、檨仔脚、苦苓脚、乌山头、 大滚水等地名。其中“茇 、 莱
、 莱 檨仔
檨仔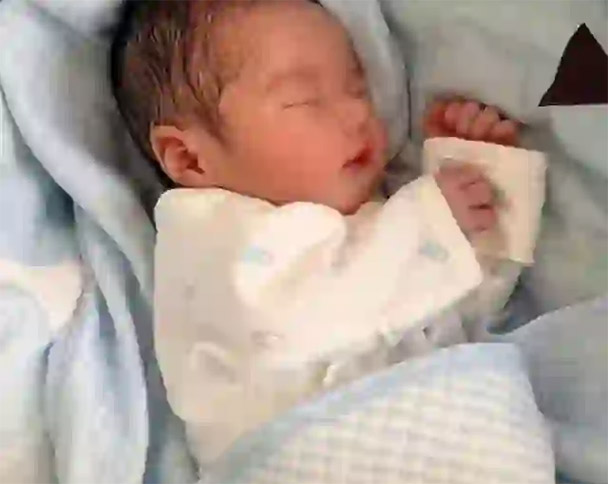 ”是闽南方言极富特色的词汇, 分别指称番石榴、菠萝和芒果,俱沿用至今。而“桶盘
”是闽南方言极富特色的词汇, 分别指称番石榴、菠萝和芒果,俱沿用至今。而“桶盘 ”和“猪 ( Thài-ti)、查某 ( Cha-bó)”更是闽南语典型的方言用语。另外, 台湾地名中也保留着一些闽南方言专用意义的地名, 如“松
”和“猪 ( Thài-ti)、查某 ( Cha-bó)”更是闽南语典型的方言用语。另外, 台湾地名中也保留着一些闽南方言专用意义的地名, 如“松 ”闽南语多用于指称“榕树
”闽南语多用于指称“榕树 ”,如松仔脚
”,如松仔脚 ; “空 ( Khang)”闽南语与“穴 (Khang)”同用, 如泉水空
; “空 ( Khang)”闽南语与“穴 (Khang)”同用, 如泉水空 ;“乌 ( O )”则是闽南语专代“黑 ( O ) ”字用, 如乌树林 ( O-chhi- n )。
;“乌 ( O )”则是闽南语专代“黑 ( O ) ”字用, 如乌树林 ( O-chhi- n )。
台湾文化属于移植型文化。移民在命名新垦地时, 也会将原乡地名文化直接移植至台湾, 以此来表露对原乡的怀念情感。如晋江县罗山乡林口村, 据《林口柯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三房柯生英、 柯惟英兄弟入台开垦繁衍, 在今台北县林口乡留下了与祖籍地同名的林口一村;另据《枫树林氏族谱》载,雍正元年泉州南安县枫树村三房第六世孙林景迪, 前往台湾花莲一带拓垦,为怀念故土在新垦地沿用祖籍地“ 枫树 ”一名。
以上闽南方言地名的分析主要借助于清代闽台两地府志、县志等史料的记载,这也表明了政府对大陆人民在台湾所创造和传播的移民方言文化的一种肯定态度, 但政府有时也对某些地名进行易名。以“噶玛兰”为例, 蒋毓英 《台湾府志》最早载其旧称“蛤仔滩”是“三十六社土番之地”,蛤仔滩 (Ha -thoan)乃音译平埔族人 Kavalan。刘良璧《重修台湾府志》里易为“蛤仔难 ( Ha-á-lan)”, 嘉庆十五年四月改译为“噶玛兰 ( Ga-m-lan)”。“蛤仔难”与“噶玛兰”写法虽不同,但用闽南语读起来却非常相近。另据《淡水厅志》载: “灵潭陂, 在桃涧堡, 距厅北五十里”。官府取“灵”的闽南语同音字“龙 ( Li ng)”代替, 改称“龙潭陂”, 成为今日桃园县龙潭乡之地名。同样的, 台湾“浊水溪 ( L -chi-khe)”在民间称为“劳水溪”、“捞水溪”, 《台湾府志》载有浊水溪“所出之水不清,流至溪亦浊”, 在闽南语发音中, “劳”、“捞”的读音 L与“浊 ( L) ”一样, 表达的意义也相同。又如,《台湾府志》记急水溪;“从大武笼山北,西过大排竹之南,又过下茄冬,经倒咯嘓之北,西迤而与嘓溪会, 同入于海”, 而道光元年姚莹在《东槎纪略》卷三“台北道里记”里提到的“汲水溪”, 就是“急水溪 ( Kip-chi-khe)”的同义词, 且“汲 ( Khip)”与“急 ( Kip)”在闽南方言里是同音字。
可见,清代台湾地名中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的形成和积淀, 虽有政府因素的影响, 但地名中的文化要素内涵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至清末, 那些入台经营贸易的洋商在记录台湾地名时更是吸收利用了大陆移民所创造出来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关于这一点,笔者特别查阅了1867- 1895年的清末台湾海关贸易报告一书, 从地名索引里出现的 160多个台湾地名 (非重复)中整理出 69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名。如海关税务司H. O. BROWN(博朗)在1875年提到的 “番薯寮”、“火烧屿”两地名,闽南语发音分别为 Hoan-chi-liu、He-sio-s,与其英文名读音非常相似。另外, 1892年署理海关税务司 F . H IRTH 在报告中指出了两个主要出口樟脑的地区: “大嵙崁( Takoham ) ”和“三角涌 ( Sankoyung)” ,通过与这两个地名的闽南语发音 ( To-khe-kham 和 San-kak-ying)相比较, 可以发现其中紧密的方言文化联系, 这也是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在台湾地名中得到很好保存和积淀的一个有力证据。如表2所示:

2
日据时期台湾地名的变更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 台湾也被割让给日本。日本统治台湾后, 行政区划变动频繁, 不仅将州辖市的城市街道名改成町名, 更是对台湾早期地名进行变更, 特别是 1920年 9月 1日至 10月 1日, 日本在台湾实施了大规模的地方行政区域改革, 对台湾早期 100多个民间地名或简化, 或蜕变为日式地名。
应该说,日本统治台湾前期, 殖民者在记录台湾地名时有不少地名仍需要借助于当地住民的日常发音, 如 1896年伊能嘉矩在台湾淡北原住民北投社做调查时, 对该词的记录为 Patao , 与其闽南语 Bak-tau读音非常接近;此外还有蜂仔峙 (Pangsie)社、 八里坌 (Palihun)社、搭搭攸 ( Tatayu)社等 地名也是如此。尤其是 1920年殖民者蜕变台湾地名,许多地名也只能在承认闽南方言读音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蜕变原则乃根据地名的闽南语读音,再以日语近音汉字 (以日语“音读”为主 )来代替。
例如彰化县花坛乡, 清代旧称“茄苳脚”,1920年蜕变为“花坛”。“花坛”日语“音读”Kadan即模仿“茄苳”的闽南语发音 Ka-tang;新竹县竹东,清代称为“树杞林”, 1920年日本人在承认“树杞林 ( Chhi -ki-nà)”闽南语读音的基础上, 以“竹东 (日语发音 Chikutou)”代替之;台北县三峡镇在嘉庆初年形成市街, 名 “三角涌”, 1920年改成“三峡”, 盖因“三峡”的日语“音读”Sankiyou近似于“三角涌”的福佬话 San-kak-yiong ;
花莲县瑞穗乡, 原为高山族阿美人聚居地, 清代称为“水尾”,1920年利用“水尾”的闽南语读音 Chi-be , 改为“瑞穂 (日语“音读”为 Zuiho)”;屏东县满州乡旧称蚊蟀, 是汉人垦民对排湾族原住民住地的称呼, 1920年改成“满洲”, 其日语读音Mansyuu仍利用旧地名“蚊蟀”的福佬话 Bng-su; 南投县草屯旧称“草鞋墩 ”, 1920年取“草鞋墩”的部分闽南语读音 Chháu-tun, 改为日语“草屯 ( Souton)”。具体变更如表 3所示。
”, 1920年取“草鞋墩”的部分闽南语读音 Chháu-tun, 改为日语“草屯 ( Souton)”。具体变更如表 3所示。

此外, 台湾地名中蜕变为日式地名的,也有根据闽南语读音, 以日语“训读 ”发音来变更的, 如高雄, 日语训读(Takao), 与闽南语“打狗 (Tan-kau)”读音相似;民雄,日语训读(Tamio), 乃利用“打猫 (Tan-niau)”的闽南语读音变更而成。
3
结语
从横向时间段来看, 闽南方言文化要素随着早期大陆移民在台开垦活动牢牢扎根于台湾土壤中, 并通过地名的方式成为了历史的文化沉淀。虽然这一文化要素有时会受到政府因素的影响, 但地名中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还是保留了下来。至清末, 那些入台贸易的洋商在记录台湾地名时, 往往也要摄取蕴含其中的早期闽南方言文化要素, 由此体现了该文化要素在台湾地名中的稳固性与延续性。
日据时期, 特别是 1920年的台湾地方行政区域改革, 殖民者强制性地将日本文化要素渗入到台湾地名中, 并对台湾早期民间地名进行变更 (包括简化、 蜕变等 ), 企图抹煞原有地名中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此淡化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但由于早期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经过长期的使用、 积淀, 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日本人将台湾地名蜕变为日式地名, 许多地名也只能承认和利用该地名的闽南语读音, 并以日语的近音汉字 (以“音读”为主 )来代替, 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 闽台间紧密的地缘关系。
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 1 期
作者:邓孔昭、陈后生
选稿:常宏宇
编辑:方梦瑶
校对:陈汶灵
审订:杨肖翠
杜诗湖湘地名考
台湾地名中的中国意识
台湾地名中的人物印记
郑氏军队屯垦及其对台湾地名的影响
台湾省地名类型和县、市级地名的演变
免费起名工具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82281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